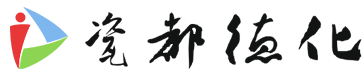乡下人家
◎ 郑文庆
晚霞下的村庄,乡间小路纵横,袅袅炊烟飘散向天空。与同事坐在石牛山的缆车上放眼四望,如此场景引我思绪万千。
我儿时生活在老家,戴云山脉腹地的一个小山村。那时候,做饭烧柴,是乡下人家无可替代的取火方式,每到做饭时间,家家户户的烟囱像开放在村子上空的花朵,平静的乡村瞬间鲜活生动起来。炊烟,或浓或稀,或长或短,总是袅袅缥缈。看多了,也就可以从冒出的缕缕炊烟判断柴火的干湿与家境的状况。一坨一坨冒着浓烟的,不用说,主人不够勤快,烧的是湿柴,煨出的是浓烟;哪家的炊烟持续时间长,说明花时间变花样地煮饭菜,家境自然殷实。反之亦然。
记忆中,老家灶台上有三口锅,最前面的是一口大锅,最为忙碌,每天都不闲着,用来做饭;中间一口稍小,用于煮猪食;后面一口最小,也没闲着,多数时间用来烧水。每天早上天边泛白,妈妈就起床,开始生火做饭。等饭做好了,我们才慢腾腾从被窝里钻出来。站在二楼,举目四望,早晨的阳光把炊烟镀上一层金边,小山村如金色的童话一般。
用木柴烧火做饭,砍柴火自然成了小孩的义务。周六日,或寒暑假,村里的同龄人邀约上山砍柴。山路弯弯,鸟儿欢悦,那时的风中飘着花香,和着青草的味道,那时的太阳温暖耀眼,天空总是纯净得发蓝。一切都那么宁静,风干的记忆留下的多为美好。
后来,外出求学、工作,兄弟姐妹六人先后奔赴各自的岗位,大概是儿时在老家生活的缘故,在城里经常做乡下童年的梦。看来,我的乡村情结已经深入骨髓了。
我喜欢乡村里那种纯朴的情感。似乎这种情感无需人为诗意地去编织,而是先天存在着,绵延不绝,犹如村里日日夜夜奔流的小溪,以及站在村尾看四季轮回的大松树。
那棵松树高大茂盛,阳光洒在葱郁的松针上,泛着绿油油的光,身躯健美,生命力茁壮。它是冬日里最耀眼的一片绿色,仿佛要在寒冷的季节里,给我们讲述一段最深情的故事。它庇护着从它如盖绿荫下走过的村人:欢跳的孩子,甜蜜的情侣,颤巍巍的老人……它,犹如一位守望者,沉淀着岁月,守护着老家温暖的一隅,滋养着父老乡亲。
我们一直在路上,走在回家的弯弯的村路上。每次回家,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,似亲切又陌生。一次又一次的回家之旅见证了我们的成长,既有欣喜又有辛酸。
每次回老家,老妈不很早就起床,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。闲聊时,老妈千叮咛万嘱咐:工作要好好干,出门在外与人为善。说着、说着,总会顺手拿出钱要给孩子们。每次回城时,大袋小袋塞得后备箱满满的。这时候,我总会嗔怪老妈:“叫你不要装,你非要装,快关不上啦!”尽管如此,每次回家,她总是乐此不疲。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无法用文字表达,所有的修辞都显得苍白。
兄弟姐妹的情感犹如人体中的动脉,血肉相连。平时,彼此之间,或许偶尔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论个脸红耳赤,但从各自的“小家”回到这个“大家”时,都会彼此放下争议,嘘寒问暖,乃至相敬如宾。每年春节,兄弟姐妹几人小聚,喝几杯小酒,边喝边聊,酒酣耳热之际,回想老爸、老妈以前的辛劳,更是无限感慨。父母在,家就在。每每其中某人有事要先离开老家时,其他几位都会目送,直至车子消失在村路的尽头。
邻里亲戚的情感则如身体中的毛细血管,纯朴真诚:强伯提来一筐新品种红心地瓜,英婶送来了时令蔬菜……仔细一想,这些丝毫没有因果和功利色彩,完全是乡下人家自然朴实的情感表达。每当农闲或雨天之时,家里的来人总是不断,或叙旧,或闲聊,或倾诉。或闲坐无事,或一杯清茶,或两盅白酒,话匣子打开了就可以浮生半日。这与城里人相见时客套的招呼乃至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“套房文化”有着天壤之别。
记得费翔《故乡的云》唱道:“那故乡的风,和故乡的云,为我抚平创伤。归来吧,归来呦,浪迹天涯的游子……”在这个新旧交替电光火石的时代,有根可寻,有故土可归,值得倍加珍视——常回家看看。带着父辈的嘱托,带着整个乡村的希望,从弯弯的村路上走来,又从弯弯的村路上走去,乡村出生的孩子这辈子怕是走不出回环反复的圈了。
已有好几天没回老家了,趁着假期回趟老家,说走就走。一路上,窗外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,那是闽中屋脊戴云山脉。戴云山麓我家乡,弯弯村路情悠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