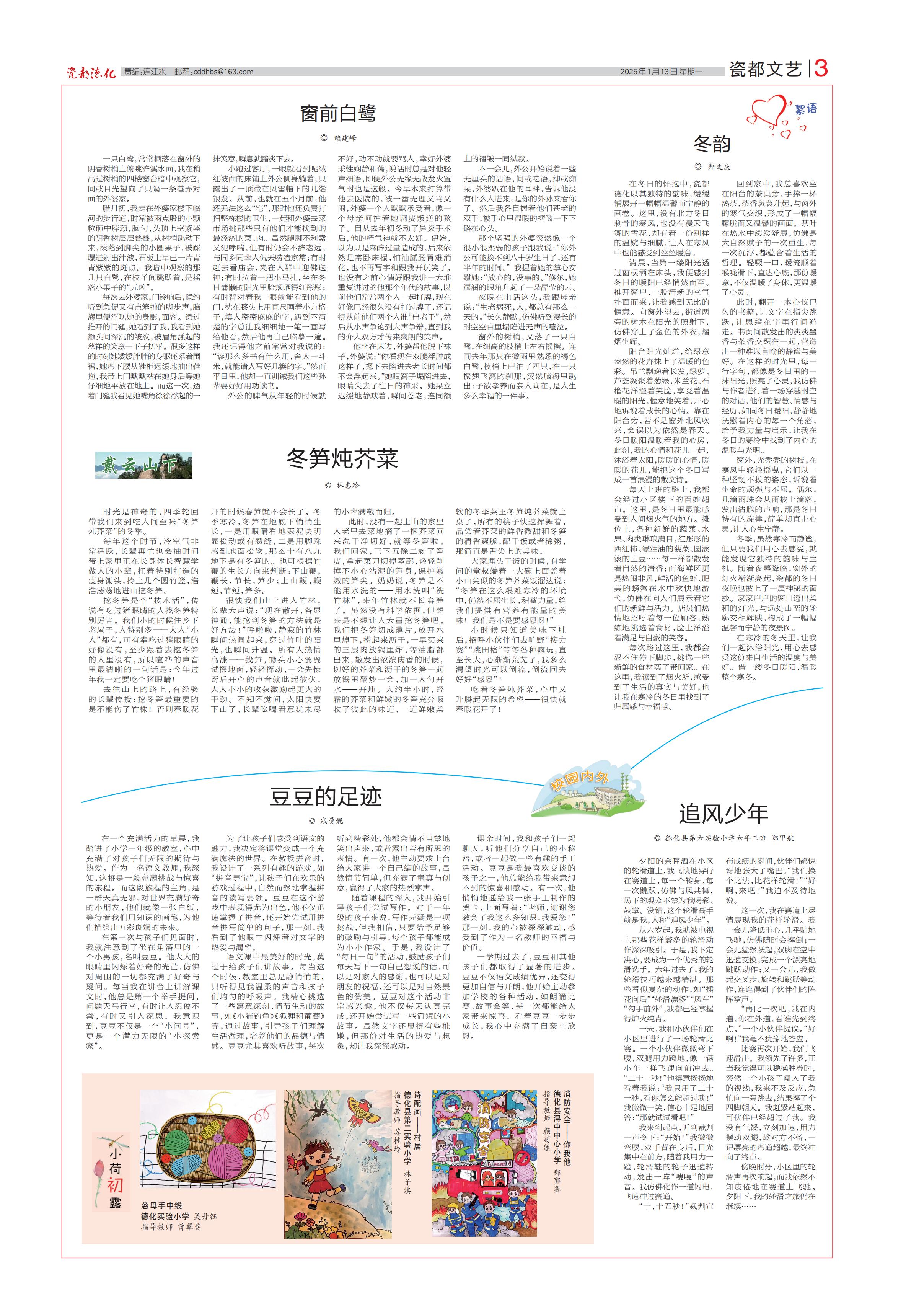一只白鹭,常常栖落在窗外的阴香树梢上俯眺浐溪水面,我在稍高过树梢的四楼窗台暗中观察它,间或目光望向了只隔一条巷弄对面的外婆家。
腊月初,我走在外婆家楼下临河的步行道,时常被雨点般的小颗粒砸中脖颈,脑勺,头顶上空繁盛的阴香树层层叠叠,从树梢跳动下来,滚落到脚尖的小圆果子,被踩爆迸射出汁液,石板上早已一片青青紫紫的斑点。我暗中观察的那几只白鹭,在枝丫间跳跃着,是摇落小果子的“元凶”。
每次去外婆家,门铃响后,隐约听到急促又有点笨拙的脚步声,脑海里便浮现她的身影,面容。透过推开的门缝,她看到了我,我看到她额头间深沉的皱纹,被眉角漾起的慈祥的笑意一下子抚平。很多这样的时刻她矮矮胖胖的身躯还系着围裙,她弯下腰从鞋柜迟缓地抽出鞋拖,我带上门默默站在她身后等她仔细地平放在地上。而这一次,透着门缝我看见她嘴角徐徐浮起的一抹笑意,瞬息就黯淡下去。
小跑过客厅,一眼就看到呢绒红被面的床铺上外公侧身躺着,只露出了一顶藏在贝雷帽下的几绺银发。从前,也就在五个月前,他还无法这么“宅”,那时他还负责打扫整栋楼的卫生,一起和外婆去菜市场挑那些只有他们才能找到的最经济的菜、肉。虽然腿脚不利索又犯哮喘,但有时仍会不辞老远,与同乡同辈人侃天唠嗑家常;有时赶去看庙会,夹在人群中迎佛送神;有时拉着一把小马扎,坐在冬日慵懒的阳光里脸颊晒得红彤彤;有时背对着我一眼就能看到他的门,枕在膝头上用直尺画着小方格子,填入密密麻麻的字,遇到不清楚的字总让我细细地一笔一画写给他看,然后他再自己临摹一遍。我还记得他之前常常对我说的:“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,舍人一斗米,就能请人写好几篓的字。”然而平日里,他却一直训诫我们这些孙辈要好好用功读书。
外公的脾气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好,动不动就要骂人,幸好外婆秉性娴静和蔼,说话时总是对他轻声细语,即便外公无缘无故发火置气时也是这般。今早本来打算带他去医院的,被一番无理又骂又闹,外婆一个人默默承受着,像一个母亲呵护着她调皮叛逆的孩子。自从去年初冬动了鼻炎手术后,他的精气神就不太好。伊始,以为只是麻醉过量造成的,后来依然是常卧床榻,怕油腻肠胃难消化,也不再写字和跟我开玩笑了,也没有之前心情好跟我讲一大堆重复讲过的他那个年代的故事,以前他们常常两个人一起打牌,现在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打过牌了,还记得从前他们两个人谁“出老千”,然后从小声争论到大声争辩,直到我的介入双方才传来爽朗的笑声。
他坐在床边,外婆帮他脱下袜子,外婆说:“你看现在双腿浮肿成这样了,摁下去陷进去老长时间都不会浮起来。”她眼窝子塌陷进去,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她呆立迟缓地静默着,瞬间苍老,连同额上的褶皱一同缄默。
不一会儿,外公开始说着一些无厘头的话语,间或呓语,抑或痴呆,外婆趴在他的耳畔,告诉他没有什么人进来,是你的外孙来看你了。然后我各自握着他们苍老的双手,被手心里温暖的褶皱一下下硌在心头。
那个坚强的外婆突然像一个很小很柔弱的孩子跟我说:“你外公可能挨不到八十岁生日了,还有半年的时间。” 我握着她的掌心安慰她:“放心的,没事的。”倏尔,她湿润的眼角升起了一朵晶莹的云。
夜晚在电话这头,我跟母亲说:“生老病死,人,都总有那么一天的。”长久静默,仿佛听到漫长的时空空白里塌陷进无声的噎泣。
窗外的树梢,又落了一只白鹭,在细高的枝梢上左右摇摆。连同去年那只在微雨里熟悉的褐色白鹭,枝梢上已泊了四只,在一只振翅飞离的刹那,突然脑海里跳出:子欲孝养而亲人尚在,是人生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