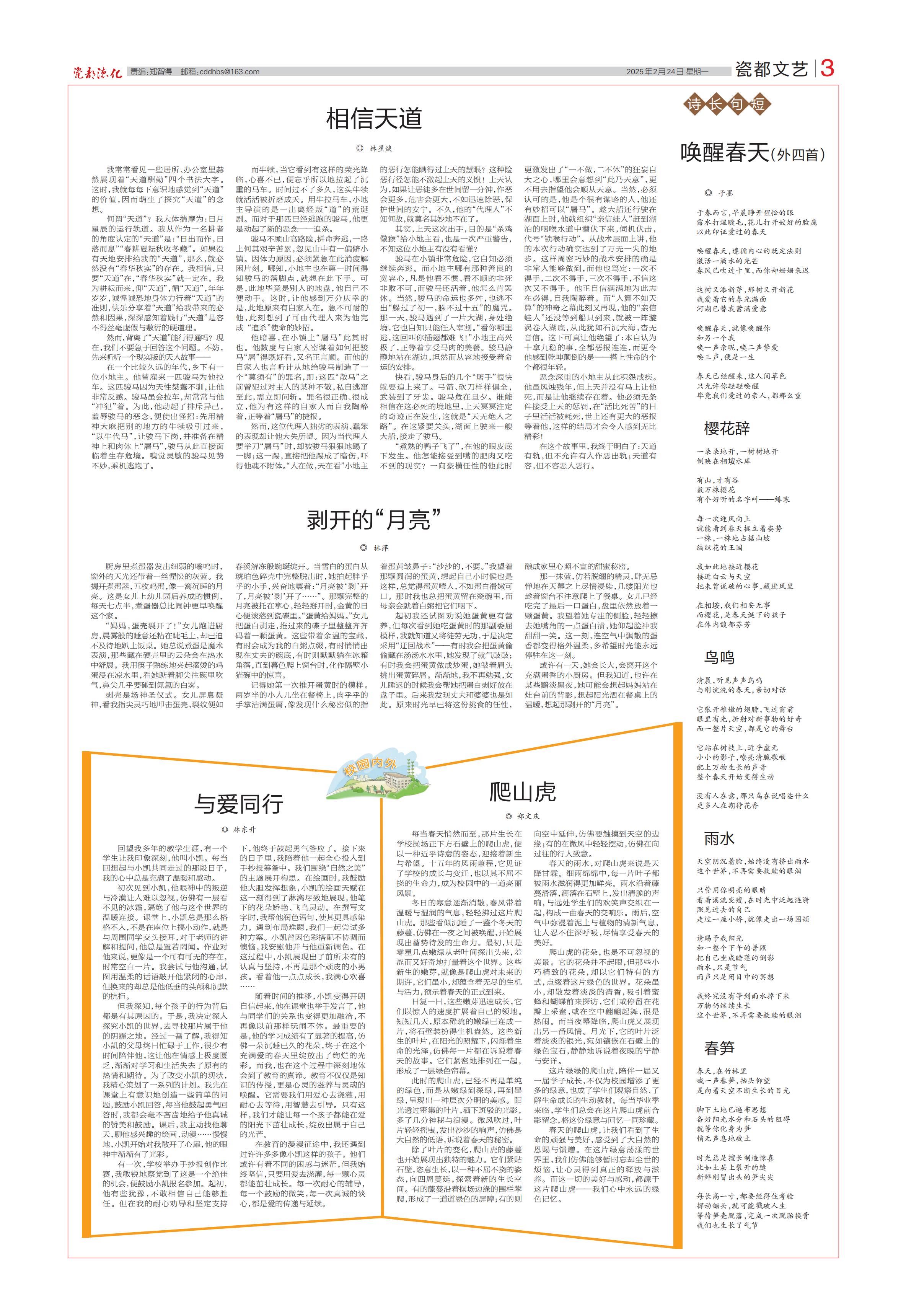厨房里煮蛋器发出细弱的嗡鸣时,窗外的天光还带着一丝惺忪的灰蓝。我揭开煮蛋器,五枚鸡蛋,像一窝沉睡的月亮。这是女儿上幼儿园后养成的惯例,每天七点半,煮蛋器总比闹钟更早唤醒这个家。
“妈妈,蛋壳裂开了!”女儿跑进厨房,晨雾般的睡意还粘在睫毛上,却已迫不及待地趴上饭桌。她总说煮蛋是魔术表演,那些藏在硬壳里的云朵会在热水中舒展。我用筷子熟练地夹起滚烫的鸡蛋浸在凉水里,看她踮着脚尖往碗里吹气,鼻尖几乎要碰到氤氲的白雾。
剥壳是场神圣仪式。女儿屏息凝神,看我指尖灵巧地叩击蛋壳,裂纹便如春溪解冻般蜿蜒绽开。当雪白的蛋白从琥珀色碎壳中完整脱出时,她拍起胖乎乎的小手,兴奋地嚷着:“月亮被‘剥’开了,月亮被‘剥’开了……”。那颗完整的月亮被托在掌心,轻轻掰开时,金黄的日心便滚落到瓷碟里。“蛋黄给妈妈。”女儿把蛋白剥走,推过来的碟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一颗蛋黄。这些带着余温的宝藏,有时会成为我的白粥点缀,有时悄悄出现在丈夫的碗底,有时则默默躺在冰箱角落,直到暮色爬上窗台时,化作隔壁小猫碗中的惊喜。
记得她第一次推开蛋黄时的模样。两岁半的小人儿坐在餐椅上,肉乎乎的手掌沾满蛋屑,像发现什么秘密似的指着蛋黄皱鼻子:“沙沙的,不要。”我望着那颗圆润的蛋黄,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,总觉得蛋黄噎人,不如蛋白滑嫩可口。那时我也总把蛋黄留在瓷碗里,而母亲会就着白粥把它们咽下。
起初我还试图劝说她蛋黄更有营养,但每次看到她吃蛋黄时的那副委屈模样,我就知道又将徒劳无功,于是决定采用“迂回战术”——有时我会把蛋黄偷偷藏在汤汤水水里,她发现了就气鼓鼓;有时我会把蛋黄做成炒蛋,她皱着眉头挑出蛋黄碎屑。渐渐地,我不再勉强,女儿睡迟的时候我会帮她把蛋白剥好放在盘子里。后来我发现丈夫和婆婆也是如此。原来时光早已将这份挑食的任性,酿成家里心照不宣的甜蜜秘密。
那一抹蓝,仿若脱缰的精灵,肆无忌惮地在天幕之上尽情浸染,几缕阳光也趁着窗台不注意爬上了餐桌。女儿已经吃完了最后一口蛋白,盘里依然放着一颗蛋黄。我望着她专注的侧脸,轻轻擦去她嘴角的一点蛋白渍,她仰起脸冲我甜甜一笑。这一刻,连空气中飘散的蛋香都变得格外温柔,多希望时光能永远停驻在这一刻。
或许有一天,她会长大,会离开这个充满蛋香的小厨房。但我知道,也许在某些黯淡黑夜,她可能会想起妈妈站在灶台前的背影,想起阳光洒在餐桌上的温暖,想起那剥开的“月亮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