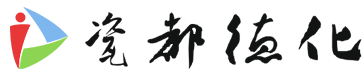德化的春天总带着三分瓷土气,那是从戴云山深处苏醒的古老记忆,在窑火中淬炼千年,化作瓷花绽放时的清响,在时光深处轻轻叩击。
瓷花,花非花。它是釉色涅槃的物质诗学,是泥与火的旷世奇恋。而对瓷花仙子郑燕婷而言,瓷花更像是生命与时间的无声对话,它记得山间的晨露,记得水碓的舂声,记得窑火中的每一次蜕变与重生。那些瓷泥在高温中凝固的绽放,是燕婷用指尖写就的时光诗篇,是她生命里对永恒最执着的守望。当我的手指轻轻抚过博古架上的白瓷牡丹,花瓣薄得能透出血管的淡青色。燕婷告诉我,一朵花要做到薄透逼真,瓷泥得揉上几十遍,每揉一遍就滤去些人间烟火气……说这话时,她的手还沾着未洗净的瓷泥,细纹里嵌着月光般的白,让我想起了史书记载的明代瓷工,“以掌纹入瓷,得天然冰裂”。而她手中的花朵,虽未入窑火,每一片花瓣却已开始绽放,其厚薄差异精确至毫米,说是既得遵循瓷土收缩的物理规律,还得暗合植物生长的自然法则。
在燕婷的瓷花艺术里,牡丹占了最多。其中,《国色天香》与《牡丹鼎》是她得意之作——花朵或恣意盛开,或含苞待放,或一株独秀,或花团锦簇,神韵自成。无论是扎根于汉白玉大理石板上,还是盛放于庄重古朴的鼎上,牡丹花姿摇曳,枝叶婆娑,娇艳欲滴中藏着盛唐的磅礴气韵。其花瓣的层次纹理,枝叶的空间动态,或花蕊的形神顾盼,每一处细节都达到了出神入化,几可乱真的地步。最妙的是花与叶之间的深情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目视久了,似乎还能听见它们的喃喃轻语……不难看出,从艺四十多载的燕婷,擅以雕、塑、捏、刻为笔,通过指尖对瓷泥的感触,捕捉到花朵绽放时气韵流转的节奏。她不仅深谙空间布局、花朵形态之道,色彩的运用更是匠心独运。她说,设色如作诗,既要懂得留白,又要在恰当处点染。那些或淡或浓的釉彩,是她与瓷泥打交道多年形成的默契。这两件作品,其形态、色彩与精神内涵,已然臻至一种近乎苛刻的完美。更为绝妙的是,当展台上的灯光亮起,光影流转制造出视觉上的动态绽放,花影绰绰。静态的瓷塑瞬间获得四维时空的延展,将其凝固的美推向诗意的无尽流动……
作品《百花争艳》通体未施丁点色料,百艳皆色白,但层层叠叠抖擞着精气神的花朵,依然让人觉得繁花似锦、葳蕤生光,盛满了整个春天的气息。不可思议的是,这一大篮子的瓷花竟然是一体成形。那仿竹编的花篮,纹理细腻如丝,腰身似少女般婀娜,篮中花卉虽然繁多,但整体上却近乎完美和谐。这和谐并非简单的堆砌与组合,而是在冲突与对立中寻得统一与协调——繁与简的相映成趣,疏与密的交织共生;雍容的牡丹与清雅的菊花,二者宛如时光的两极;而在繁密的花丛间,那刻意留出的细细疏朗,恰似春风穿过的缝隙,将生命的律动凝于其上,使得整件作品既充满动感又透着沉稳大气。细细观察花朵,卷曲与舒展,意态潇洒,生机勃发,即使是一根小小的花蕊都处理得神采飞扬。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巧妙联结,让整件作品更具视觉震撼,也让我看到了燕婷对大自然的虔诚摹写。
众观燕婷的瓷花作品,足见她深谙花的形态与气韵,却又不囿于此。在她手中,瓷花既是自然的写照,亦是心灵的归宿,是她独一无二的“精神庇护所”。她说赏花观气,真正的瓷花不在形似而在神韵,一定要让瓷土铭记花开时的呼吸,才可做到无香蝶也来。她深信瓷土自有灵性,瓷花创作是一场灵性的叙事,一件上乘瓷花佳作既要有外在美,更要重现泥土之于花朵的根源感。然而,要做到这一点,并非易事。需要对各类花卉生长了然于心,还需洞察其隐匿美感。
谈起瓷花创作初衷,燕婷笑言自己如同寻梦的旅人。她自幼随父亲郑子添学习釉下青花设计,1983年9月到德化瓷厂工作,其间跟随杨剑民、苏玉峰、陈德卿等大师学习陶瓷雕塑。1986年,拜师景德镇陶瓷学院梁任生教授,后又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。那些年,她在泥与火的交织中摸索,在形与神的边界上徘徊,直到某一天,她听见泥土传来的呼唤——原来最动人的雕塑,是让泥土记住花开的声音。那一刻,燕婷发愿要做出永不凋零的花,用瓷土定格自然界转瞬即逝的美,将脆弱的花卉凝固为永恒的审美符号。岁月流转,她手中的花朵愈发栩栩如生,因此她被业界誉为“瓷花仙子”“瓷花皇后”……
此刻,燕婷手持竹刀,在湿软的瓷土上反复推敲。她说这看似简单的花瓣弧度塑造,实则是对植物生命密码的破译。还说,瓷花最初只是瓷器的点缀,像一位羞怯的配角。或在杯壶边缘上轻轻绽放,或栖息于瓶罐的肩头,或依偎于仕女的鬓边,用细碎的花语诉说着无声的故事。直到1915 年,德化苏学金一枝瓷梅花横空出世,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摘得金奖。这是瓷花首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,不再依附于任何器物,不仅开创了陶瓷花卉创作新领域,也成为陶瓷雕塑题材的一次重大变革。
燕婷的婆家祖辈许友义,正是苏学金的得意门生。他创作的瓷花作品既有整株带盆的,也有不带盆的,形态各异。在时代的跌宕变迁中,燕婷不仅继承了这份匠心,更在传统中开辟了新径。她钟情于挂盘与屏风,让瓷花在平面上焕发出立体的生命——机器滚压的瓷盘平整如镜,釉色里泛着时光的涟漪;手工编织的镂空瓷盘,则似江南园林的花窗,将光影裁剪成诗;而木制镂空屏风,俨然成了一方移动的庭院,让盛放于上的瓷花在虚实之间翩翩起舞。当阳光穿过镂空屏风,瓷花的影子便在地上织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有时,燕婷会将瓷花与手绘山水相融,让花瓣间流淌着云雾,让花枝与飞鸟共舞;偶尔,她也会让仕女佳人隐现于花间,似在诉说着一段段未了的梦境,引人遐思。
从审美观念的角度来看,时代变迁在陶瓷设计中最鲜明的体现,莫过于新观念的引入。而对于艺术而言,时尚的内涵远不止于潮流,它既可以是传统元素的延续,也可以是设计师个人情感及理念的综合表述。如若说燕婷的瓷花作品是在传统根基上的一种现代创新,那么她创作的《生活》无疑是她对现代审美观念的又一次重塑。
泥片直接成型的《生活》,是燕婷参加“罗小平雕塑•泥片成型塑造艺术研修班”时的作品,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较浓,与传统瓷花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它以深邃的黑色为背景,三枝灰白新荷挺于其上,叶边弯曲,或高或低,或正或侧,其不规则的形状和肆意挥洒的线条,构建出一个自由而富有张力的艺术空间。这空间叙事手法,与宋代山水画中的“留白”传统形成跨时空对话。尤其是对比鲜明的色彩,不仅避免了画面的单调与乏味,更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与立体感。虽是西方印象,但燕婷巧妙地运用了一些微妙的纹理与光影效果,形成类似宣纸晕染的墨韵效果,使得荷叶更加立体与生动。特别是在光线折射下产生的朦胧光晕,这种视觉效果暗合道家“大象无形”的美学追求,充满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。
正当我感叹燕婷用瓷土构建了另一种永恒的生命图景时,她却淡然说道,这种以土为纸、以火为墨的创作,不是简单的自然摹写,而是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辨。作品《生活》,更多体现了对“存在与虚无”和“自由与束缚”的探讨——背景的大片黑色,象征着虚无与未知,而灰白色新荷则在虚无中凸显出来,成为存在的象征;然而,欲绽未绽的荷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背景的限制与束缚,暗示着自由并非无限制的,而是在一定框架内的相对自由。
就在这一刻,我终于理解了燕婷内心深处的挣扎与释放。诚如她在《生活》中要表达的“生的喜悦,活的顽强”一样,在坎坷的人生中无论生活多么苦涩,她都是微笑着把最美丽的花朵呈现给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