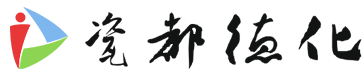走在西安街头,逛得有些乏了。同行的朋友提议说:“去吃碗面吧?”“不要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不知怎的,我从小就对那白生生的面条提不起兴致。看吧,它软塌塌地趴在碗里,像一团泡发后没了筋骨的白棉线;若是汤面,更是糊作一团,夹起来时拖泥带水,溅得满桌汤汁,讨厌!有时候,它倒也不那么黏糊,可干巴巴的,毫无生气,就那么死气沉沉地堆在盘中,叫人看了便倒胃口。
“面痴”陈姐拽着我走进了面馆,笑着说:“来西安不吃面,等于白来一趟。”菜单上密密麻麻的面食名称让我眼花缭乱:biangbiang面、油泼面、臊子面、裤带面……
最先上桌的是biangbiang面。当服务员端上来时,我惊讶了下——每根面条足有5厘米宽,1米多长,数了数碗里只有三根面条,却铺满了整个碗面。热情的服务员告诉我们,“biang”字为陕西特有,连字典都查不到。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这个字的来历:相传清朝时有个穷秀才,为换一碗面汤喝,就造出了这个字。说着还给我们念起了顺口溜:“一点飞上天,黄河两边弯;八字大张口,言字往里走……”我不以为然地拿起筷子,心想:横竖都是面,能有多特别呢?吃完第一口脑子里就跳出一个词“劲道十足”,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口感,多一分太软,少一分太硬。酱料在嘴里游走,让人回味无穷。
口中的面还未吞下,便听到“油泼面来咯”。只见服务员将一碗滚烫的热油浇在辣椒面上,“滋啦”一声,香气顿时四溢开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挑起一根面条送入口中,先是感受到辣椒的刺激,接着是芝麻的醇香,最后竟然品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麦甜。这味道层次之丰富,完全颠覆了我对面食的认知。
最让我惊艳的,竟是那碗看似最寻常的臊子面。明明是再家常不过的食材,面条并不宽长,烹饪手法也不见花哨,可端上桌的瞬间,我的目光竟像被磁石吸住般挪不开——五颜六色的配料在青花瓷大碗里铺得一丝不苟,仿佛谁把彩虹裁成了细片,又精心码出了章法。金黄的鸡蛋皮切得匀匀整整,像撒了层碎金;黝黑的木耳蜷着边,透着油亮的光泽;鲜红的胡萝卜丁艳得晃眼,衬得翠绿的蒜苗愈发精神;就连雪白的豆腐,都透着股温润的莹光。这哪是一碗面,分明是幅刚从画纸上走下来的水彩,连颜料的晕染都带着恰到好处的灵动。
我小心翼翼挑一筷子送进嘴里,先是臊子的醇厚在舌尖炸开,接着鸡蛋的香、木耳的脆、胡萝卜的甜、蒜苗的清、豆腐的嫩争先恐后地涌上来,最后竟在喉咙口汇成一股熨帖的暖。这滋味,“好吃”二字怎能概括?
本以为这份震撼是源于我这“非面爱好者”的少见多怪,转头看向身旁的陈姐,却发现更令人惊讶的画面:前一秒还在与我们天高地阔闲聊的她,此刻头几乎埋进了碗里,筷子翻飞间,面条被吸得“滋滋”作响,嘴里塞得满满当当,连说句话的空隙都没有。要知道,陈姐可是出了名的“面痴”,三餐不离面,南北各地的面几乎尝了个遍,论起吃面的资历,没人比得过她。
可就是这样一位“阅面无数”的行家,此刻也吃得毫无架子:碗底的最后几根面条被她用筷子仔细扒拉干净,随后端起碗,仰着头把汤底一饮而尽。放下碗时,她额头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,却还意犹未尽地咂咂嘴,冲我感叹:“这面,真是绝了!”
在西安的这几天里,我几乎尝遍了当地所有的特色面食。每走进一家面馆,都能发现新的惊喜:有的面条宽如裤带,有的细如发丝;有的劲道弹牙,有的入口即化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这些看似简单的面食背后,都凝聚着西安人代代相传的智慧与匠心。
如今回到南方已经十余天,但西安的面香似乎还在唇齿间萦绕。我终于明白,西安人吃的不仅是一碗面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那筋道的面条里,是关中平原千年的麦香;那滚烫的热油中,是西北汉子豪爽的性格;那亮眼的色彩下,是市井百姓最质朴的生活热情。一碗寻常的面食,却蕴含着最深厚的生活智慧。我想,这就是西安面食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吧。
“晚上想吃什么?”正欲停笔,耳边传来爱人的询问。
“去吃碗面吧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