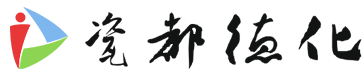当青花沁入璞玉胎釉,中国白便有了蓝色心跳。
邂逅这蓝色心跳,我的心如恋人相见般雀跃不已。那是春末夏初交替时节,前往红旗坊的途中,我的脚步驻足止余斋。这条路、这斋房,皆是初访,斋房外墙上“让非遗艺术走进生活”牵引着我。彼时的我,从未想过久违的浪漫心跳,竟会在此怦然重现。

引得我心潮澎湃的,不过是小小体积的青花瓷杯。一朵常见的牡丹,一只亦属常见范畴的蝴蝶。只是呵,瓷如玉,青如黛。温润瓷骨中透出的微光,将青花晕染成深浅不定的梦境。在通透如冰晶的杯壁上,光影似乎有了呼吸,那抹凝烟蓝美得流动起来——牡丹徐徐绽放,蝴蝶翩跹起舞。而另一只杯中,一尾锦鲤从璞玉般温润的瓷胎里游了出来。最为神奇的是,牡丹花瓣、蝴蝶翅膀、锦鲤尾巴竟呈现出“墨分五色”的奇妙效果……执杯对光,竟能透影见指,青线清晰如春蚕吐丝。光线穿透之际,更生奇妙折射——既非全然剔透,亦非全然朦胧。随着光影流转,细如发丝的蓝色纹路在白色瓷胎间若隐若现,恍若春溪于冰层下静流。不得不叹,本已至纯的冰种玉瓷,托起青花更显其清逸;青花的墨韵又反衬白瓷澄澈。二者相生,恰似昆笛遇流水,墨砚对春山。久久凝视中,我的呼吸与心跳,漾起绵绵欢喜……
德化,制瓷历史远溯至夏商时期,所产白瓷被世界誉为“中国白”。而青花的钴蓝,亦在德化的烟火里流淌了四百余年。对白瓷之美可说早已司空见惯,对白瓷胎托起的青花神韵,我亦是了然于心。无论是自由洒脱的国画写意,还是极尽精微的工笔描摹,皆因青花落笔处是德化瓷特有的莹白而别具艺术魅力。尤其是德化白瓷中的冰种玉瓷和高冰瓷,接近玉石的质感,让钴蓝与素白的相遇,于素朴中更见磅礴生机。众知,高冰瓷乃在冰种玉瓷的基础上,提升玻化程度和透明度而成,瓷胎愈发细腻温润。然而,眼前这杯子的质地,分明比高冰瓷更透,更润,亦更衬青花之幽美……
就在我对杯子质地犹疑不定时,一位身着素净白衫、玄色布裙的姑娘迎上前来。那身姿如新竹初拔,步履从容,落落大方,可微垂的眼睫与颊边悄然浮起的淡霞,又分明透着几分腼腆。她的面庞生得很是秀气,脂粉未施。眉眼清亮,似两泓映着晨光的浅溪。就在两人相视的刹那,一缕山间晨风带着露水气息的清新,在周遭的空气里自然流转了起来……直觉告诉我,这青花杯出自她手。
果不其然。她告诉我,这是璞玉瓷,是在高冰瓷的基础上通过真空窑烧制而成,比高冰瓷更温润细腻。她是余丽萍,自幼喜欢美术,2008年高考后从家乡尤溪来德化陶瓷学院求学。也就在那年,学校开设了青花研习班,她成了第一批学员。有次创作,她故意让青花釉料在素坯上自然晕散,竟幻化出绝妙的瓷上水墨。也是在那时,她深刻体会到了“青分九阶”的神奇,如痴如狂地爱上了青花。生性恬淡的她,对青花却有着近乎执拗的爱恋,夜以继日地在老师的工作室埋头研习青花手绘技艺;即便在2019年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后,她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院教授青花,就是扎在工作室里独自创作。就这样坚持了近二十年。凭借娴熟的青花分水技法,她不仅闭着眼都能在方寸瓷面上营造出远山近水的空间意境,更是让青花在冰种玉瓷的澄明之境中恣意流淌,任情写意。

“寻常白瓷胎骨疏松,青花落笔仿若浮于绢帛;璞玉瓷玻化胎骨密如凝脂,反令青料沉稳沁胎,线凝神聚。”丽萍执杯,引我至一款名叫《随园诗画》青花瓶前。瓶身上漏窗梅枝间,一戏装美人宛然。其云鬓簪翠,璎珞玲珑,净如秋水素面上眉眼含情,笑意温婉,气韵自成……丽萍说道,多年随师精琢戏曲人物,悟得昆曲水袖与青花笔意有异曲同工之妙——皆以线条的虚实变化传递情感。故特意将宽大水袖设计成半透明质地。当光穿袖褶,青纹摇影瓶身,宛若戏台上水袖起舞。
今年年初,璞玉瓷惊艳亮相,胎透如冰。丽萍初见,蓦然想起《随园诗画》中的水袖,心弦无端轻颤。多年创作经验告诉她,透亮似初凝脂膏的璞玉瓷,不仅将“中国白”的空灵澄澈推向极致,也将为青花艺术更精微的表达开辟出更为澄澈、饱满的新境。
正如丽萍所预见,因璞玉瓷胎通透若冰莹润似琉璃,愈显青花墨韵之灵动。尤其是璞玉瓷的釉下青花,借助独特的分水技法,蓝与白不再是机械的依附关系,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生命交融之态。
“璞玉之美在于本真,青花之韵在于无痕。一件上乘的璞玉青花,既要坚守瓷胎本真,又要让青花活起来。”言罢,丽萍俯身于素胎前,手中饱蘸釉水的青花笔,笔锋游走如履踏水痕,随性而赋意,恰似昆曲的水袖迤逦而行……
这一刻,心跳复又怦然。这璞玉青花,应是最美中国白吧。